 過去的事情記憶清晰,是因為它難忘,過去的事情記憶模糊了,但還要回想它,是因為它有意義。數十年前餘西鎮的人和事,在我記憶中有清晰的,也有不清晰的,但都有回想的意義。
過去的事情記憶清晰,是因為它難忘,過去的事情記憶模糊了,但還要回想它,是因為它有意義。數十年前餘西鎮的人和事,在我記憶中有清晰的,也有不清晰的,但都有回想的意義。
一、我與餘西鎮
我出生于通州的二甲鎮,我母親出生于通州的餘西鎮,二甲鎮距餘西鎮約5華裡。母親幼時,父母雙亡後由二甲鎮的高家收養,叔叔曹筱晉,嬸嬸吳克勤對母親關懷備至,數十年來母親視叔叔、嬸嬸為親生父母,而我從小未曾見過外祖父、外祖母,也就将曹筱晉和吳克勤視作嫡親外祖父、外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故居在餘西鎮,按當地的習俗叫長輩前常加一些特征的詞,故我就叫曹筱晉、吳克勤為餘西公公、餘西奶奶。小時候能去的親戚家不多,故常去餘西鎮,因為餘西公公見我聰穎乖巧常誇我,并給我好吃的東西;再因餘西鎮離二甲鎮不遠,步行一會就到,所以我就成了餘西公公、餘西奶奶家的“常客”。
至今我仍時常想起餘西鎮鎮頭有座高橋,鎮上有一條古老的街道,街裡有一座牌坊。外公家有一個小院子,院子裡有一棵高大的銀杏樹,有一群比我年長的學中醫的大哥哥、大姐姐……
二、餘西鎮的高橋
餘西鎮的高橋是指幾十年前,鎮的東南端架在通呂鹽運河上的一座石作橋梁。因經過餘西鎮的通呂鹽運河段不寬,再加河岸兩側的房屋緊鄰河道,橋梁無法建長,估計在三十多米,因鹽運、客運量大,船隻體量大,橋拱起的橋洞也須高大。這座橋的體量不大,橋身長度與高度比較接近,中間橋面至水面的距離估計應在二十米左右,所以這座橋感覺特别高,人們都稱它為“高橋”或“餘西高橋”。
兒時的夏日,總有膽大的小夥子看到橋下無船時跳水嬉戲,當初,我将這些小夥子視為“英雄”,現在想想覺得很危險,因為“高橋”确實很高,隻有“英雄”才能一躍而下。
高橋是二甲鎮到達餘西鎮的必經之地,每當我推着自行車從高橋上經過時心裡總有居高臨下,威風凜凜的感覺。而從兩端橋頭下坡時總喜歡提早蹬上自行車,以感受從橋坡上駕車“滑翔”的快感。
悠悠歲月,通呂鹽運河水緩緩而行,高橋下過往大小船隻川流不息,高橋上人群、車輛南來北往。多少年來高橋不管是酷暑嚴寒,還是白天晝夜,都是默默地承重身上的壓力,疏理身下的繁雜,運載着兩岸的福祉,推動餘西鎮的日新月異……高橋對餘西鎮人民具有無量的功德,餘西高橋是偉大的,它應載入餘西鎮發展的史冊。
社會在發展,交通載體在變化,現在餘西高橋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鋼結構的平橋。我無意對鋼結構橋的功能、結構進行評價,我隻是贊美過去高橋的形式與功能,因為高橋是我心中最低調、最完美的橋。餘西的高橋在造型上既有南方的嬌柔之美,又有北方的陽剛之氣。
我成年後去過江南諸地,觀賞過江南的各種小橋,我還是認為餘西的高橋是最美的。上海朱家角的放生橋沒有餘西高橋高聳、氣派;江蘇周莊的雙橋沒有餘西高橋便捷、直率;浙江烏鎮的三橋沒有餘西高橋堅實、穩固。……我贊揚餘西高橋的美麗是因為餘西的高橋一直承載着我兒時的美好記憶,承載着我對家鄉深深的眷戀。

印象中的餘西高橋 高祥生工作室制作
三、餘西鎮的龍街
小時候聽大人說,餘西是一塊龍地,龍地必然有龍的傳人。就近現代而言,餘西也是英才輩出,僅我知道的餘西的英才就有曹大同、曹頂、曹文麟、朱理治、曹筱晉等,最近又聽說共産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的一位妻子潘蘭珍也是餘西人,還有我認識的曹衛星……這些餘西名人、英才的資料在諸多文獻中俯拾皆是,我再贅述有恐不完整或不準确。因此,我還是談談我記憶中的龍街為妥。
數十年來龍街基本上沒有改造過,它是原汁原味的曆史文化古街。龍街的建築體量不大,形制不高,年代也不久遠。整條街大多數是一層平房,少數二層樓房顯得很突顯。龍街的建築和餘西鎮的其它建築基本上都是硬山屋脊,兩坡屋面,鋪小青瓦,其中也有歇山屋脊的,但數量很少。從龍街建築形式看,龍街應是在宋以後建造的。
龍街的建築樣式無疑是南方的,與江南小鎮舊城區的平房樣式相似,這可能與餘西場的原鹽民為江南的移民有關,所以龍街雖地處蘇北,但建築還具有江南的特點。
龍街的建築、龍街的街道、龍街的街面、龍街的牌坊尺度都不大,等級也不高,但在形制等級、空間尺度、用材規格、裝飾紋樣上相互都是協調的。
龍街不長也不寬,我記憶中三、四十年前的龍街的兩側有各種店鋪:有賣雜貨的、有賣布匹的、有賣水産的、有賣中藥的……似乎比現在的花式品種多,街上也比現在熱鬧。東西兩側店鋪之間距離不大,兩側的店員和對喊話也能聽得清清楚楚。龍街并不長,抽煙的人,從街頭到街尾走完都不會抽完一根煙,龍街的街面是大塊岩闆與小塊碎石片相間鋪地,具有江南傳統街道鋪地的特色,……龍街的建築與吳家欣先生所著《餘西古鎮的曆史與現狀》一文中的“餘西鹽課司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官署設立,帶來了一些配套機構設施……才夠建起一個市鎮的格局。……”說法一緻。

餘西的龍街 高祥生工作室制作

餘西的龍街 高祥生工作室制作

餘西的龍街 高祥生工作室制作

餘西的龍街 高祥生工作室制作
龍街的中部有一尊為褒揚郁氏美德,旌表節孝功績的乾隆年間禦賜,并興建的節孝牌坊。龍街節孝坊形式為單門,雙柱,四層梁坊,雙層頂蓋,柱礎設夾袍,節孝牌坊高5餘米,寬3米,牌坊所有構件均為磨光灰色花崗岩。牌坊自乾隆26年建成至今250餘年,曆經滄桑,雖有桂子等局部構件有風化現象,但總構件基本完整,未見明顯殘缺,這對古建的保持、維修是有利的。節孝牌坊的體量、尺寸與龍街現在的空間尺度是協調的,節孝坊在龍街上是突顯的,但又不過分誇張。所以無需對牌坊做體量,形制上的擴大,否則會改變龍街的整體空間尺度。
現在的龍街未曾做過大的改造,建築、牌坊、街道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貌,真誠的希望倘若改造這條曆史文化街道,應維護龍街原來的尺度、形态,特别不能人為的擴大原來的空間尺度、建築形制,因為龍街現在的面貌在當今未改造過的曆史遺産中是稀有的。
雖然龍街的建築形制不高,倘若改造,形制不高就按不高的形制改造,不高的形制也需要做出不高的典範。

餘西的龍街的節孝坊 高祥生工作室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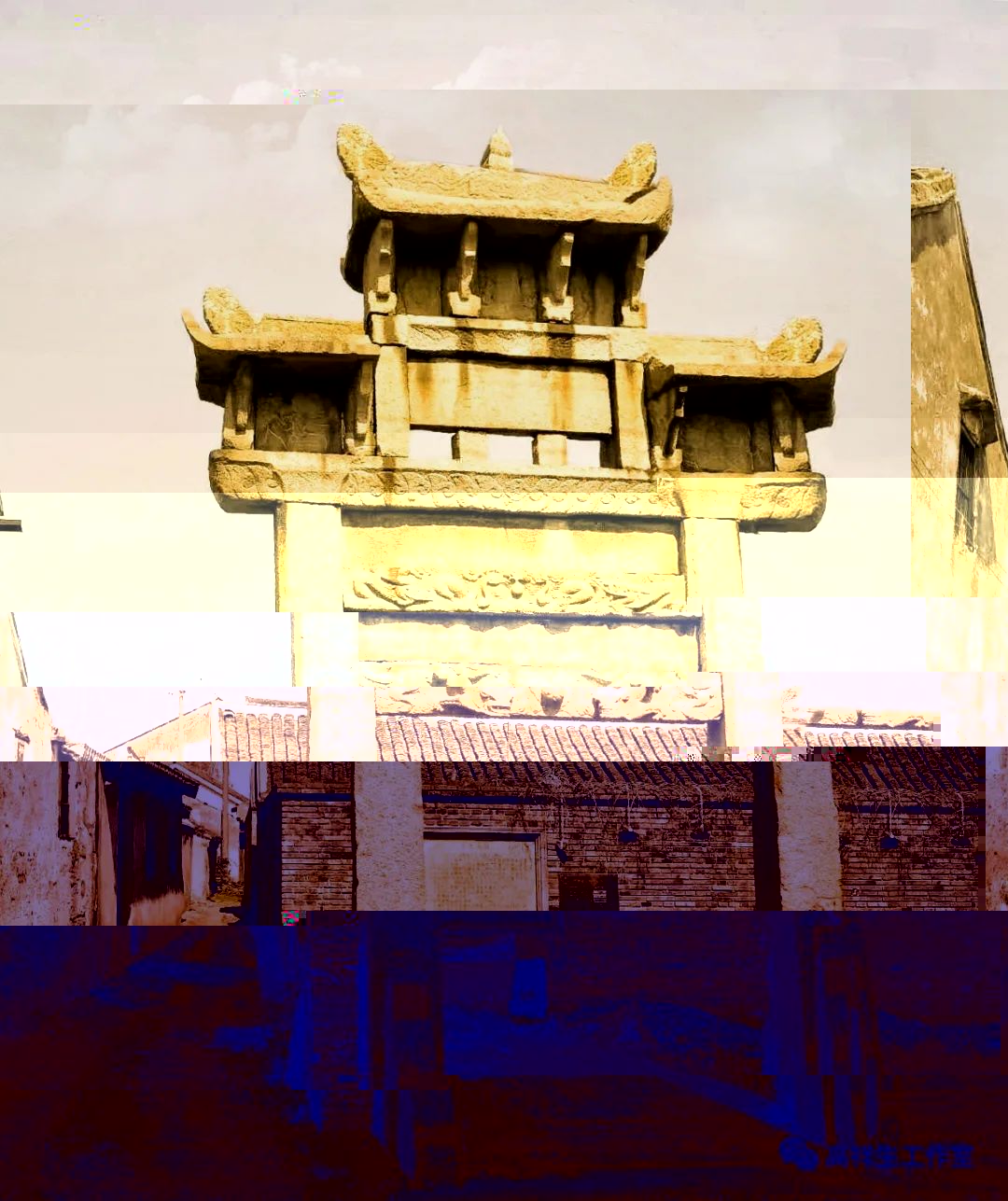
餘西的龍街的節孝坊 高祥生工作室制作
四、餘西公公家的銀杏樹
在龍街牌坊的一側有條數十米長的小巷,走過小巷就是我餘西公公家。60年以前,餘西公公還沒有去金沙組建南通縣中醫院,有一段時間他就在餘西家中行醫的。
餘西公公的家在一個小院中,小院朝東的房間是公公、奶奶等家人生活、會客的房間,家中除公公奶奶之外還有大姨夫李武俊、大姨曹育新、二姨夫王興相、二姨曹一新、三姨夫錢元洪、三姨曹又新,奶奶的弟弟吳茂龍,姨妹姨弟明明、華華和紅衛。小院朝南的房間是公公和幾個學徒行醫的房間,我印象較深的學生有季光、曹允中、唐俊、邱祖萍、曹銀等,小院的房子是舊的,朝南、朝東兩排房子加起來不到200㎡。兩排房子都是硬山屋脊,鋪小青瓦,地面是小青磚和綠草相間鋪設。牆面的粉飾已陸續裂落,大都裸露出青磚的縫障,有些縫隙中還爬着綠草……小院北側的建築和設施是簡樸的,但小院的南邊卻打理得别有情趣。
小院的南邊有一小花園、花園中種了菊花、月季、佩蘭、鳳仙、盆栽的有金絲竹、金桔……花的品種不多、但都很雅緻,很有文化人的情趣。
小院的東南角有一棵年代久遠的銀杏樹,雖然樹的産權不屬公公家,但樹栽在小院中,給我帶來的視覺感受使我日久生情,并經久難忘。小院中的銀杏樹無疑是我童年、青年時期看到的最高大、最漂亮的樹,小院中的銀杏樹在餘西鎮的大多位置都能看到。我曾多次與朋友講過我餘西公公家的小院前有一座清代的牌坊,小院中有一棵高大的銀杏樹,餘西鎮上都能看到。……
銀杏樹對氣候、土壤及環境的要求不高,它耐高溫、耐寒冷,一年四季都生長得很好。每逢春天這銀杏樹就披上一層新裝,一簇簇葉子,嫩綠嫩綠的;夏日,銀杏樹格外枝繁葉茂,它給半個小院遮陽、防暑:秋日,檸檬黃色的葉子中夾雜着若隐若現的小白果,美麗而誘人,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白果,所以銀杏樹又叫白果樹;秋日銀杏葉逐漸的由綠葉蛻變成黃綠、檸檬黃色、黃褐……然後在秋風中抖落,在秋風中像蝴蝶在小院的上空飄來飄去;冬天,大雪紛飛,銀杏樹被上一層銀裝,但屹然挺立,此時小院裡的地上、窗台上都灑落了黃色的、褐色的仍然散發出淡淡香味的銀杏葉。
聽說銀杏樹的葉子可以做成銀杏葉片的中成藥,銀杏樹的主幹可以做砧闆,銀杏樹的樹材可以刻字、做雕刻,銀杏樹的一身都是寶,銀杏樹的一身都是奉獻給社會的财富。
這些都三四十年前的事了,但我還是經常想起餘西鎮的舊貌、餘西公公的小院和那棵英姿飒爽、碩果累累的銀杏樹,令人魂牽夢萦。我總是在想餘西公公不就像一根高大挺拔的銀杏樹嗎?他将一生獻給了通州、通餘一帶的黎民百姓,他嘉惠杏林,福佑鄉老,他的一生獻給了祖國的中醫、中藥事業,他功德無量。
現在銀杏樹已不在,餘西公公也走了,但那種美好的人和事,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永遠留在人間,留在我心中。

